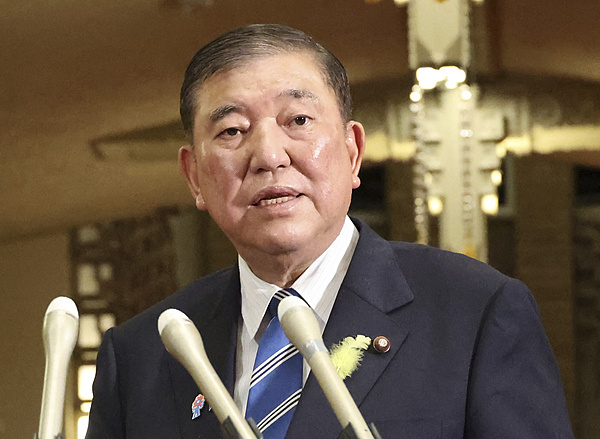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寻访上海抗战遗迹,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
若是以上海的公园作为线索,也会浮现出一段屈辱与抗争交织、伤害与坚韧并存的抗战史。
公园是上海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上海的公园充当着避难所和民众集会的举行地,也有一些被日军征用为集中营或驻地,还有不少公园在战火中被毁,只能从文献和记忆里找到它们的历史。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在她看来,承载战争记忆的场所多种多样,仅以“抗战建筑”难以涵盖,若用“抗日战争纪念地”这样的名称,既可以包括四行仓库这样的纪念建筑,也可以指各种类型的避难所,甚至是更多已经消失的重要建筑与构筑物遗址地。
“在城市中挖掘更多有特殊记忆的抗战纪念地,形成追溯历史的行走路线,是很好的构想。这非常不易,因为城市建设带来剧变,许多建筑已经消失,太多痕迹已被淹没”,卢永毅说,“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例如,抗战时期上海的大量公园都曾用作临时避难所,她建议,“是否可以以立牌或铺地设计等形式唤回记忆?”
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为例,卢永毅指出,它既是战争纪念地,也是非常出色的战争纪念馆。宝山曾是两次淞沪抗战的主战场。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位于友谊路1号的宝山孔庙的大部分建筑被日军炸毁,只剩下大成殿幸免于难。1956年,在孔庙旧址上扩建起了一座长江边的公园。2000年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公园内落成开放。2014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公园进行改建,纳入更多淞沪抗战的内容,并从“临江公园”更名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2015年,改建后重新开放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采用"馆园合一"的模式,将纪念馆与公园环境有机结合。走进公园,能看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碑,还有“汇聚”“历史涟漪”“结-1937”“历史之门”“警示钟”等一系列室外纪念艺术装置。纪念馆内则展出了抗战时期的电文、手令、战役总结等文书,以及官兵家书、嘉奖令、电影胶片,以及军械、军服等物件,还原了当年的抗战场景。

上海松湖抗战纪念碑
卢永毅认为,抗战初期的老城厢、闸北地区和江湾地区,都因日军轰炸遭受严重破坏,对于那些战时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即使没有任何遗迹留存,也可以结合公共区域、社区空间甚至商业环境,设计安排纪念地标志。”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记忆里的公园
“文庙公园——在小西门文庙路,系将文庙旧址改筑而成,故名。园占地不广,而池沼花木,点缀得当,可供游览,园中有演讲厅,每日演讲通俗故事。此外有图书馆、一二八战迹陈列馆,及卫生标本陈列所等,昔之祭堂仍保持原状,陈列各种礼乐祭器。园之对面为市动物园。”民国时期出版的《上海市大观》里记载了文庙公园的建立和布局。这段史料出现在《上海公园:1868—1949的城市景观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作者王继峰介绍了近代上海公园的各个侧面,其中也包括抗战时期的公园所承担的用途。

文庙公园旧影
抗战前,公园是上海市民重要的娱乐和社交场所,曾有露天音乐会、夏季夜晚避暑的“夜花园”、赛龙舟等各种活动和游乐项目。战争爆发后,公园里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都被连根拔除,取而代之的是与战争的正面交锋。抗战胜利后,热闹鲜活的公园图景或许随着公园被毁而消失,但至少还留在当时人们的记忆里。如同《上海公园》里所记录的南市居民对文庙公园的回忆:“城南毁了,流寓上海长久了的人,对于文庙公园,一定会有着深刻的怀念的,我相信。尤其在城南居留过的人更不会忘记文庙公园那清新的风景所给予的好感。”
1931年,文庙公园内筹建市立民众教育馆,这一建设因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而一度停顿。1932年6月1日,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及市立图书馆在文庙公园正式成立开放。图书馆为市民读书看报、学习知识提供了理想场所,平均每日到馆阅读人数大约有六七百人,诞生于抗战烽火下的民众教育馆则举行过不少民众聚集的抗战活动与教育普及活动,文庙公园深受当时的市民喜爱。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南市遭日军飞机轰炸,文庙公园和图书馆被炸毁,民众教育馆停止活动,只有庙宇幸免于难。
同样在南市,由沈家花园扩建而成的半淞园原是游人如织的公用私园,1918年10月1日《申报》曾报道其“花木溪山应有尽有”,开放时“必有车水马龙之盛也”。半淞园东南濒黄浦江,西至西藏南路、苗江路,北达中山南路。抗战爆发后,半淞园被炸为废墟,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棚户区,后来改为工厂和民房,如今只留下一条半淞园路来追忆。

半淞园旧影(图片来自《江南园林志》)
从战争纪念地到抗战纪念馆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朱宇晖看来,抗战建筑大致上可以从功能和事件的角度进行划分。“有些建筑的功能专门为战争服务,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承担过跟战争行为紧密相关的功能。比如松江的醉白池,池上草堂被改成了日式建筑,供日本驻军享乐。”
1937年11月9日,松江沦陷,醉白池被日军占用。除雪海堂、宝成楼外,所有堂轩亭榭都改成日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醉白池重新修复,将日式装修拆除,恢复原貌。
“另一类建筑是和抗战的重要事件紧密相连”,朱宇晖说,“比如轰动一时的虹口公园爆炸案。”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庆祝日本天长节,当时的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等7人都在阅兵台上。韩国抗日义士尹奉吉假扮日本人混进会场,突然朝台上投掷一枚炸弹,白川义则和上海日本居留民团行政委员河端贞次直接被炸死,另外五人被炸伤,爆炸发生后,尹奉吉被日军逮捕,最终在日本金泽就义。

鲁迅公园内,纪念尹奉吉(号梅轩)而建的梅亭
虹口公园最初是以体育活动为主的综合性公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被日军占领。后来由于鲁迅墓的迁入和鲁迅纪念馆的设立,改名为鲁迅公园。1994年,为了纪念抗战义士尹奉吉,公园里设立尹奉吉义举纪念地,建有梅亭、梅树和碑石,因尹奉吉号“梅轩”,其纪念馆取名“梅园”,占地8500平方米。
公园里的“和平之道”
在今天的虹口区霍山公园里,有一条“和平之道”。2015年,为纪念犹太难民避战的历史,霍山公园完成改建,这条“和平之道”在公园里诞生,兼具游览、纪念、文娱活动三种功能。此外,霍山公园里还安放了一座“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纪念碑,用中、英、希伯来语三种语言纪念中犹人民互相支持、共同迎来抗战胜利的历史。

霍山公园里的“和平之道”
霍山公园位于今霍山路118号,已有百余年历史。二十世纪初,许多西方侨民与虹口居民共同在这一带生活,其中14户侨民联合筹集资金,租赁了汇山路(今霍山路)和惠民路之间的一个小角落,将其打造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之后在工部局的批准下改作公园,起名“斯塔德利公园”。20世纪20年代初,因公园对面辟建舟山路,而改名舟山公园,1944年6月更名为霍山公园。

霍山公园铭牌
1943年,日本占领当局发布有关“欧洲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的公告,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该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犹太人无法走到隔离区以外的地方,而处于隔离区内的霍山公园(当时仍为舟山公园)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霍山公园也成为了犹太难民重要的避难所和集会场所。霍山公园见证了和平的来之不易,如今又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休憩场所,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
在虹口,另外还有一些经历过战火的公园,如今都已经以各种形式获得了重生。虹口区的汇山公园和霍山公园一样,曾是战时犹太难民的避难和休息场所,1950年,公园改为互动工人俱乐部。昆山公园曾经历过多次破坏,在1940年时被日军占为临时集中营。上海解放后,重新平整土地,修复道路,向市民开放,之后又经历过多次改造设计与重建。在昆山公园的中央,一棵150多岁的皂荚树始终立于原地,见证了这里的沧桑巨变。

昆山公园老照片

昆山公园的皂荚古树 图源:微信公众号“上海虹口”
“建筑的重建具有象征意义。建筑可以被用来修补建筑环境,使被粗暴撕裂的伤口固定下来,或者将原来的生活线条重新编织在一起,恢复以前的生活。这样做为保存共同记忆树立了新对照物。”在《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里,作者罗伯特·贝文论述道,通过重建,日常建筑被赋予了纪念性,“重建就使它们成为纪念建筑,为了让人们铭记导致它们被毁的事件。”这一点,也能在上海很多公园的重建里体现。而在抗战胜利80年后的今天,重新提起这些昔日的公园,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纪念。